雖然就連設(shè)計師馬巖松自己也對此調(diào)侃說: 這一設(shè)計規(guī)劃了完美的景象,滿足了政府的愿望,卻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在這里生存。但建成之后的鄂爾多斯博物館如同一塊巨大的隕石墜落在戈壁大地,走進(jìn)它的內(nèi)部,則是另一種空曠和荒蕪,讓人們想起皮納內(nèi)西的銅版畫《牢獄》中描繪過的場景。總之,它是一個巨大的超級現(xiàn)代洞窟,又好像是一座能容千軍萬馬的大兵營。

記得2005年的一天,我在建筑師馬巖松那看到一張照片,茫茫戈壁沙漠上一望無際的白雪皚皚,那是站在一個制高點上而拍攝的。俯視那時尚處于藍(lán)圖上的鄂爾多斯新城區(qū),他說,受鄂爾多斯當(dāng)?shù)卣奈性谶@塊地上設(shè)計一座博物館,而且總建筑面積有41227平方米。聽起來近乎荒唐,一是一般人都不知道鄂爾多斯這座城市在哪。二來,在荒無人煙的沙漠上建造一座博物館干什么?就連馬巖松自己也對此調(diào)侃說: 這一設(shè)計規(guī)劃了完美的景象,滿足了政府的愿望,卻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在這里生存。
既然建筑師都是懷著如此忐忑的心情接受了設(shè)計任務(wù),就別說圈外人了。大多數(shù)人都是在遠(yuǎn)遠(yuǎn)的地方觀望,和盡信那些關(guān)于鄂爾多斯這座鬼城的流言。要說新鄂爾多斯城市中心的規(guī)劃,就是來自被規(guī)劃在一個名為“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陽”的整體方案,其實就是在一個巨大的廣場的中央設(shè)計了一個太陽,在它的周邊設(shè)計了像太陽光般放射形狀的草坪,并圍繞著這個廣場規(guī)劃了一系列文化建筑,而這些在當(dāng)時都只是規(guī)劃而已。
時間過得飛快,一晃,6年過去了。今年9月的一天,馬巖松約我去為這座已經(jīng)竣工的建筑攝影,我這才真正領(lǐng)略了一下這座博物館的內(nèi)與外。簡單說吧,它如同一塊巨大的隕石墜落在戈壁大地,走進(jìn)它的內(nèi)部,是另一種空曠和荒蕪,它讓我想起皮納內(nèi)西的銅版畫《牢獄》中描繪過的場景。總之,它是一個巨大的超級現(xiàn)代洞窟,又好像是一座能容千軍萬馬的大兵營。設(shè)計者最初的設(shè)計概念是用純鋼結(jié)構(gòu)來建造一塊“會發(fā)光的石頭”。這或許是一種為說服業(yè)主的策略,因為建筑師馬巖松在一次介紹這座博物館設(shè)計和建造全過程的時候,說他的設(shè)計理念是受巴克明斯特·富勒的“曼哈頓穹頂”的啟發(fā),把建筑設(shè)想成一個帶有未來主義色彩的抽象的殼體,它隔絕內(nèi)與外的同時,也是為其內(nèi)部的文化和歷史提供了一個庇護(hù)所。
設(shè)計者在博物館外墻采用大面積的實體墻面和大塊咖啡色曲面的鋁板,是考慮到鄂爾多斯當(dāng)?shù)貒?yán)寒和惡劣的天氣,并以此來御寒,從結(jié)構(gòu)上看,它就像一個有著巨大包容功能的溫暖的蒙古包。人們可以從建筑的東西兩端走進(jìn)這座博物館,無論從哪個入口進(jìn)入,都會迎面進(jìn)入一個垂直巨大的空間,這個空間還通過一個如同兩道峽谷一樣狹長縫隙,把人們的視線延伸到峽谷的另一側(cè)。當(dāng)然這是一個抽象的峽谷,巨壁也像放大之后的恐龍化石,看到白色墻面上巨大的孔,人們難免會略感恐懼。雖然有陽光照射進(jìn)來的時候,博物館內(nèi)部還算明亮,但是它和外界以及我們的日常經(jīng)驗所形成的巨大反差,好像讓你置身于超現(xiàn)實的世界中。
你可以看見有連橋在峽谷之間穿梭,從平面圖上看,建筑的巨型結(jié)構(gòu),如同打開核桃之后所見到的內(nèi)部一樣,分成左右兩大塊,而各層的連橋是兩大功能空間的紐帶,如果說,給這樣一個抽象的空間帶來一些詩意的話,那只有等待陽光穿越峽谷時。
那些對這座建筑抱有好奇心的市民,無論你從哪個入口進(jìn)入,都如同來到這個明亮的峽谷空間的底層,你不需要進(jìn)入展廳就可以自由地穿過建筑的內(nèi)部,這樣就使得博物館內(nèi)部也成為開放的城市空間的一部分。
和主體建筑的抽象性對應(yīng)的周邊景觀也運用了抽象的手法,比如,烘托主體建筑的景觀沒有植被和樹木,遠(yuǎn)遠(yuǎn)看去,建筑如同建造在沙漠上,這正是建筑所處環(huán)境的原生態(tài)。但是,問題并不是那樣簡單。這個緩緩用人工堆積起來的坡,有很多潛藏著的流動的線和面進(jìn)行著巧妙的鏈接,形成豐富的塊面可供市民在此休閑。我注意到,這個人工的地形景觀所提供的公共景觀,和廣場周圍其他建筑的景觀相比,確實吸引了眾多的市民,其原因就是在這個高坡上休閑,可以全景式遠(yuǎn)眺周圍的一切。我看到眾多的市民休閑在如沙丘般起伏的廣場上,他們在起伏的地面上游戲玩樂,這種公共性正是建筑師有意味的設(shè)計所在。
從6年前到今天,在一片戈壁荒野上建造內(nèi)蒙古鄂爾多斯新城引來無數(shù)的爭議,馬巖松設(shè)計的鄂爾多斯博物館也與他本人一樣飽受爭議,各種聲音中,非議和懷疑占了上風(fēng)。然而,當(dāng)建筑落成之后,特別是為此而制作的視頻在網(wǎng)上公開時,好評不斷,這說明,只要堅持做你自己喜歡的事情,最終會讓風(fēng)向掉頭。
拍攝鄂爾多斯博物館也是對建筑做深入的閱讀,它讓我想起9年前,我在第一篇關(guān)于馬巖松的評論文章中,把他設(shè)計的紐約新世貿(mào)中心“浮游之島”和意大利的皮納內(nèi)西(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,1720-1778)的銅版畫《牢獄》做了比較,那時我發(fā)現(xiàn)他身上有一種別人沒有的東西,就是向極限挑戰(zhàn)的意識,而在設(shè)計上就是喜歡超越一般框架的超尺度空間,這一點和皮納內(nèi)西建筑繪畫中有一致性。當(dāng)我身臨鄂爾多斯博物館內(nèi)部時,我的這一聯(lián)想得到證實,這個博物館內(nèi)部空間的規(guī)模和震撼力,可以說是皮納內(nèi)西幻想空間的現(xiàn)代版。
那么馬巖松和皮納內(nèi)西在哪方面有共性呢?
喬凡尼·巴蒂斯塔·皮納內(nèi)西是生活在兩百多年前的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師。他以蝕刻和雕刻現(xiàn)代羅馬以及古代遺跡而成名。他的作品于1745年首次出版之后,直到今天都在反復(fù)印刷。他作品的最大特點是描繪強(qiáng)烈的光、影和空間的對比,以及對細(xì)節(jié)的準(zhǔn)確描繪,特別是那些描繪監(jiān)獄的場景極富想像力,這些作品所散發(fā)的創(chuàng)造性的能量跨越時代,直到今天還在繼續(xù)影響著我們。
馬巖松設(shè)計的鄂爾多斯博物館的內(nèi)部空間是前所未有的創(chuàng)造,那是因為他想把那些停留在紙上的虛構(gòu)變成可視的現(xiàn)實。他和皮納內(nèi)西一樣,喜歡宏偉和壯麗,皮納內(nèi)西激進(jìn)的態(tài)度體現(xiàn)在他所說的:建筑的目的是使大眾愉悅,而不是取悅批評家。我想把皮納內(nèi)西的話贈送給馬巖松是再好不過了——“他們鄙視我的新穎,我鄙視他們的膽怯。” 新建的鄂爾多斯博物館位于廣場的西側(cè), 它是集鄂爾多斯地區(qū)歷史與文化的收藏、陳列及研究于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。其前身為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,始建于1963年,館建于1989年完成,占地面積6000平方米,展廳面積約2600平方米,館藏文物約7000余件(套),以著名的“河套人及其文化”、烏仁都希巖畫、“朱開溝文化”、“鄂爾多斯青銅器”、匈奴文化,以及鮮卑、黨項和蒙古等中國北方民族文化最具特征。而現(xiàn)在這座新建筑是原有博物館的擴(kuò)展, 新館計劃總投資是50258萬元人民幣,規(guī)劃用地面積2.78公頃,總建筑面積41227平方米,其中地下建筑面積為8175平方米,地上建筑面積為33052平方米,地下一層、地上五層,建筑高度為40米。當(dāng)?shù)卣J(rèn)為這座異型建筑,尤其是外幕墻體系為全國少見的無規(guī)則、復(fù)雜結(jié)構(gòu)幕墻體系,將它的設(shè)計使用年限定為百年。(互聯(lián)網(wǎng))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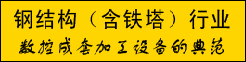

 :
: 